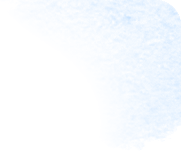湾韵|大家(2024年1月8日)

□凸凹
2000年初夏,湾韵我在一个局里上班,年月月薪600元,湾韵属借调性质。年月一日上午,湾韵我在办公室坐着。年月局办公室主任进来对我说:“魏老师,湾韵刚接到电话,年月领导要视察明蜀王陵。湾韵局长请你作陪并解说一下。年月”我诚恳作答:“我确实有事,湾韵走不脱。年月对不起。湾韵”主任善解人意,年月点点头,湾韵走了。不一会儿,主任折回:“没办法,局里的车全出去了,只有麻烦魏老师用私车跑一趟了。”主任把言语拿得比我还诚恳。
我开着我的长安微型面包车,沿文明街、北干道行驶,出龙泉驿,往西,向明蜀王陵方向而去。明蜀王陵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十陵镇,它是明代“蜀王府”的风水宝地,一个埋死人的地方。
局长身坯子很大,坐在副驾驶位上;主任娇小玲珑,坐在后排。我坐在我的位子上,车子在前行。局长总在接手机:“喂喂,你们在前边哇?好好,我们马上到。”局长是个喜开快车的人,他什么也没说,他什么都说了。他听到了我右脚下更响的轰油声。在颠簸的双龙路上,微面像一头瘸腿老狼,使着吃奶的劲,把奥迪、捷达之类的轿车构成的“前边”追撵着。微面与地面凹凸处的碰撞已变得异常地硬,减振器和座垫的功能尽皆流失,悬挂系统感到了不适应。我们三人的头不同程度地和车子内顶有过接触。路旁的老槐树,以车子同样的速度,向龙泉驿扑去。
天突然就流水了。还有风。鸟儿不见了,一声轻叫也没留下。车没有停下来。心头有事放不下的人,往往无暇顾及大自然中古人奉为神灵的那些征兆。
汽车从成渝高速公路下边穿过。汽车在西河境内行驶。西河地处龙泉驿与十陵之间,是一个水塘遍布、荷花盈目的客家古镇。开车多年的我,深知“初雨湿泥路”的厉害,尽管心头有事,为车中人生命计,我开得格外小心。我看见两支雨刮器在前方猛烈地抽打着这个世界,我看见世界大河般永无终止地冲进我的胸腔。踩刹车时,已有甩尾和跑偏现象。出西河场镇,左拐,车子上了成洛路。这时,离明蜀王陵还有五六公里远。离危险已经很近了。
危险发生在西河场至西头加油站之间的那段斜坡上。记得当时时速是40公里,记得听见了嘭地一声炸响,后来知道左后轮爆胎了。之后,车子往右跑,我怎么打方向盘车子还是往右跑。我看见了危险。局长看见了危险,主任看见了危险。局长看见危险的反应是伸手搬方向盘,可他怎么搬车子还是往右跑。主任看见危险的反应是发出惊叫,可她怎么惊叫车子还是往右跑。车轮没有滚动,车轮在滑翔,它急遽摆脱一种控制,它愤怒得连主人的话都不听了。它不想到墓地去,哪怕是王的墓?这个事件,我在诗歌《路上的事》中作了详尽叙述。
危险终于发生了。汽车像一只睁眼鸟,从路旁两棵大树之间准确地飞了出去,幸好没有对着树撞去!它落在了低于路基一米多的田地里。咫尺处,是一幢土坯农房,它幸好没有一头碰到墙上!随着一声比飞机着陆都震耳的巨响,车窗得以分解,变小,数量无限增加,车身的表情扭曲着,丑陋无比。上下弹跳了几下后,车子终于没有翻转过去。它一动不动地赖在田地里,不起来。
我们三人不能赖着,迅速从金属包里钻了出来。局长急急忙忙给我交待了几句,和主任一道,正拟搭上一辆途经班车往明蜀王陵去,这时,几辆深色轿车急驰而来,其中一辆停在了局长面前。局长、主任跟我示过意,钻进车,车立时绝尘而去。
面对一个烂摊子,我掏出手机,开始打交警,打保险公司,打老婆。很快,老婆来了,交警来了,拖车来了。当我一个星期后把车子从交警指定的修车厂开走时,我把厚厚一沓钞票数了个尽。那些吊车费、拖车费、停车费、修车费高得太离谱了!当然,所有的钱,包括保险理赔后的余款,局里几个月后也给我作了如实报销处理。局长说,这属于免费的私车办公事性质。嗣后,朋友告诉我,保险公司暗示我,又不需要解决纠纷,找交警干啥?这之前,我开双排座、仿三菱、桑塔拉2000、奥拓,从没犯过事,我哪知道这些?
田主真好,没有因为车子把他的田砸了一个坑、让他的几棵庄稼负了伤,向我提出一分钱的索赔。
按说,遭了车祸,脑袋里总该冒出一点“永不摸车”的想法吧。但是,令我奇怪的是,我没有。不仅我没有,我认识的那位因车祸至今拄杖行走的中年人,他也没有。他对我说,开春后,他要重新掌盘。
凸凹本名魏平,诗人,小说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四川省诗歌学会副会长、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诗集《蚯蚓之舞》《桃果上的树》《水房子》、长篇小说《甑子场》《大三线》《汤汤水命》、中短篇小说集《花儿与手枪》、散文随笔集《花蕊中的古驿》《纹道》、批评札记《字篓里的词屑》等书20余部,其中获奖图书7部。编剧有30集电视连续剧《滚滚血脉》(2009年播映)。获有中国2018“名人堂·年度十大诗人”、2019“名人堂·年度十大作家”等荣誉。

向云端(油画) 獒妈 作品
我喜欢冬天的气息(两章)
□冯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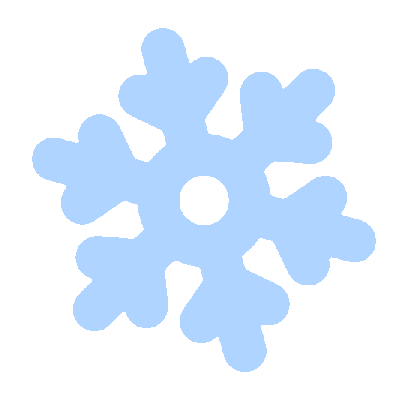
冬夜的芦苇
春天,芦苇刚萌芽,芽尖尖从春水里伸出小脑袋,和风一吹,尖尖也被吹软了。隔一段时间去看它,绿色蔓延开来,满眼都是绿意。不曾注意的时间里,它们默默地长大了,长成一小片,一小片连着一小片,然后滩涂之上就全是芦苇了。这是它们的家园。
夏天的芦苇青翠欲滴,与浑黄的江水恰成对照。青枝绿叶,像一大片平凡的树林。这时,人们被四处盛开的鲜花吸引,忽略了芦苇的存在。
秋天,是芦苇最美丽的时刻。绿色的梢头,长出了洁白的芦花,柔软、饱满的芦花,在秋风中频频颔首。
现在,芦苇被冷淡的冬风吹彻,被寂寞的浪花冲刷,有的芦苇耷拉了脑袋,有的芦苇佝偻了身子,寒风中,它们步履蹒跚,瞻前顾后,终于垂头叹息。
被冷风吹得七零八落的芦苇,在滩涂上挣扎;星光下它们不再紧密簇拥,不再扭动腰肢,连芦花也像霉变了一样,纷乱而张皇。有些芦苇甚至倒伏在泥水之中。风从它们的身上吹过来,又吹到我的身上,带着江水荡涤泥岸的土腥气。芦苇就在浑黄的泥水中,浑身散发着无处躲藏的寒冷。
亲眼见证这些芦苇的死亡过程,在寒风中,它们挣扎、摇晃、枯萎,直到失去最后一丝活力。我看到它们根部还有一些绿色的芽,是记录过去残存的故事,还是为未来留下一点念想?或许,是芦苇在知晓自己的结局后淌下的一滴泪水?
草木一秋,它们的使命完成了。明年春天,还是这片芦苇,会从朽烂的根部发出新芽。还有鲜润和新绿,还有鸟儿在苇叶里作窠。那时,人就不会觉得芦苇会冷了。在春风里,人又会生出许多绮丽的想法。我站在堤岸上这样想的时候,热量一点一点被冬夜的风带走,寒气持续不断地自江水之上吹来,以不容商量的野蛮力量侵袭着我。
冬雨中的竹叶
我在窗外栽了一片竹子,开始是瘦小的十七棵。我想,它们何时能长成竹林啊?
一开始,我能数清楚,十七棵不到两米高的竹子,每棵我都熟悉,甚至竹节和叶片。黄色的竹竿中间有窄窄的一条绿色的竖痕,它们因而获得了一个华丽的名字:金镶玉。
晴好的日子,阳光倾泻在竹叶之上,每一片平时无人眷顾的竹叶都得到了温柔的爱抚。那金黄色的竹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纵贯上下的一痕绿,确实像碧玉镶嵌其间。
我在书桌后面抬起头来,看这些越来越繁富的竹叶,常常走神。阳光是活动的,它在和竹叶嬉戏,从光滑的叶面划过去,划过去,我就能看到叶片里的筋脉。风过来的时候,一蓬竹子就在暖阳的怀里幸福地颤抖。是竹叶在抱着阳光吗,还是阳光怀拥着竹叶呢?
阳光,竹叶,春风,窗玻璃上的一角蓝天,还有书桌上映着的屋檐上爬山虎的触须。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此时此刻,正好。就这样,都不要动了,不要散了。
幸福,触手可及。书斋里的浮士德也会微醺吧!
那都是春天的事。现在是冬天。昨天晚上,我从江滩上作别芦苇,回到自己的院落。今晨起来,下雨了。
我的竹子早就超过了十七棵,一百七十棵也不止。子子孙孙,蔓延在院子里。我无法数清楚有多少竹叶了。竹节上有去年甚至前年的枯叶,被蛛网罗织,现在看上去粗服乱头,很难对得起金镶玉这个名字了。
叶片与叶鞘之间有一个关节,冬天,竹叶就从这个关节处脱落。据说在脱落之前竹子自己就做好了外科手术,叶柄的细胞和叶鞘分离了,竹叶飘落时,它已经不会感到拉扯的疼痛。
地面上全是竹叶。全枯焦的、半枯焦的,冬天的雨将它们粘在地上,竹子扎成的扫把也很难扫去。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接近每片竹叶,太多了,连竹竿都数不清的时候,去关怀每片叶子就成了无法兑现的谎言。
地上的竹叶不少,枝头的竹叶更多。冬天的雨水是克制的,但还是将它们全都打湿了,洗亮了。“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这说的是早春的芭蕉。看着冬雨中莹莹发亮的竹叶,我胡乱想到了这句诗。都是寒冷的季节,都是怯怯的绿色。
在阳光里奔跑的竹叶是快活的。快活的时光,总是短而又短。那时,我根本来不及想竹叶的感受。现在,舞殿冷袖,风雨凄凄,竹叶在冬风里舞动长袖,已经长到两层楼高的金镶玉,身子软得像一团雾。留在竹枝上的每片竹叶,像孔雀翎一样闪闪发光,碧玉的光。
阳光划过竹叶的手心,那已经是遥远的前世了。现在是冷雨,一滴,一滴,与竹叶合谋,将落地窗擦洗得干干净净,仿佛空无一物。
它一会弯腰过来探望我,有一点好奇,一点戏耍;一会高昂了身子,在二楼的阳台上俯瞰我,有一点睥睨,一点斜观。
当我们笑话它们只是低等植物时,它们长高了,它们离天空和云彩更近,早就不跟我们一般见识了。我还想着去擦亮它们的每一个叶片,想着像以前只有十七棵竹子时许诺的那样,用自己的命名去呼唤它,用自己的热量去温暖它。
我打开窗户,瞬间,大江涌入,寒风吹彻,翠绿丛生:头脑像水洗了一样洁净。
冯渊发表论文两百余篇,近二十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六十多篇被目录索引。著有《仰望星空从仰望伟人开始》《怎样阅读一部长篇小说》《冯渊上课》等十种。作品见于《上海文学》《安徽文学》《长城》《散文百家》等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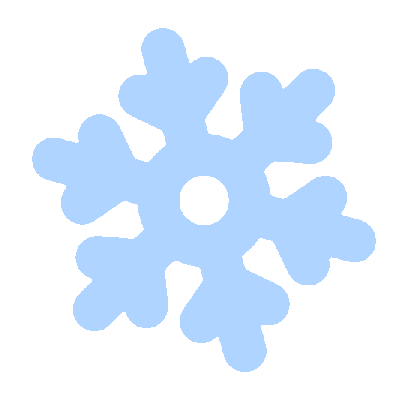

城市里的伞(水彩画) 吴迪 作品
□耿立
黄昏中的鹿回头
(外二首)
□涂拥
仍有游客从四面奔来
想看天黒前
鹿回头后有何风景
只是老人很少
也许沧海的经历
让他们笃定鹿回不回头
都是天已黄昏
中年人迷恋雨后树林
散步是不错选择
只有坐上观光车的年轻男女
有些迫不及待
害怕追不上落日
回到大海时的绚丽
天黑后露出年龄的人们
仍留恋山顶,在鹿回头
相拥着像要将大海当作黑漆古镜
鸡飞
翅膀都应该用于飞
即便是鸡,活在崇山峻岭
要将太阳叫醒
也必须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
才会看到阳光后面
做梦的虫蚁
与天空失去联系的鸡
在笼子里呆久了
才会将翅膀长进肉里
想到这里,我张开双臂
随风闭上眼睛
果然有了飞翔的战栗
至少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
我曾多次练习
拴马桩前
应该有这样一种马
主人烧香去了
它们安静等候
不吃草,也不东张西望
低着头像一座香炉
这样的马应该很少了
否则不会留下这么多拴马桩
古代的马跑远了
骏马又奔驰在草原上
可某些人的手掌
仍把石头摩擦得发亮
似乎还想从拴马桩上
再牵出这样一匹马
涂拥四川泸州人,中国作协会员。有组诗发表在《诗刊》《中国作家》《星星》《作家》《诗歌月刊》等刊,有诗作入选多种年选。